从一座繁华的内地城市到拉萨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飞机的速度令我们惶恐不安,我们担心这种轻意的进入是对一座伟大城市的不敬。
从一座繁华的内地城市到拉萨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飞机的速度令我们惶恐不安,我们担心这种轻意的进入是对一座伟大城市的不敬。相信每个人看拉萨有自己的眼光,诗意的现实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我们选择几中直接的方式来呈现拉萨,它们只是一些侧面或缩影,让我们在更近的距离内看到拉萨的内部。
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旅游者,他在八角街会看到什么?
商业繁华背后古朴的文化存留是我们刻意的捕捉,至于女人、状态、飘这些看起来与拉萨莫不相关的词汇则是我们无意中的发现,它们丰富了拉萨的概念,也令更多的旅游者从中体会到了发现之美。
我们只用最简单的方式和途径呈现了一个旅游者眼中的拉萨,我们动用了让你感觉亲切的语言和意象,我们看到的拉萨有想象中的爱情、浪漫、诗意和恍惚,更有现实中热闹、质朴和挡不住的商业气息。
这便是拉萨的真实状态。
八角街是一个神人共处的地方。在这里,喧闹的跳蚤市场与庄严宁静的寺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走在拉萨的八角街上,你会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八角街与神灵世界一墙之隔的街道(文/尼玛甲绛 图/明可)
拉萨的中心
我住的香巴拉酒店就在八角街旁边,朝里走几分钟就是有名的大昭寺。住在这条街上很方便,有几家颇有特点的小酒吧。酒吧兼具画廊的功能,而且供应从酥油茶到咖啡、尼泊尔小煎饼、西餐等几乎所有的食品,能上网,在里面消磨一个寂寞的晚上是很愉快的事情。
门外就是八角街了,那些从西藏各地走来的藏族人穿着他们传统的服装,披挂着各种色彩的由绿松石、珊瑚石和金银、珠宝镶嵌而成的装饰品,象是复活了一个已经湮没在时间中的戏剧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拉萨其实就是八角街。其实八角街的真正概念并不仅仅是条环行街道,而是围绕在大昭寺周围的那一整片古旧的,有着白墙、黄墙、花窗和经幡错杂,并不时有人在僻静的街角处小便的街区。八角街上的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灿烂,麻雀的啾啾声从街道两旁的廊檐下倾泻下来。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鲜亮的色彩,无论是街道两旁的建筑,还是热闹非凡的街边小摊上千百种待售的物品,这些色彩最终形成了我对拉萨的第一个印象。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到拉萨的原因,多少还是有些反应。在酒店里找出一种叫“高原胺”的药片,吞进肚里,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八角街上。流转的人群迅速地把我带到大昭寺门前的广场上,在那里,朝圣的人围绕在正门的石碑和香炉前,在袅袅的烟雾中,对着神灵顶礼膜拜。每个人都双手合什,微闭着双眼,嘴里喃喃有声。藏族人的生活离不开转经,他们手持转经筒,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地绕着具有宗教意义的物件或地方转了一圈又一圈,只是想在轮回的命运中寻求更美好的来世。这转经筒内藏经文,筒身隽刻着佛教的六字真言,每转动一下,就等于将经书念了一遍,十分节省时间。另外还有一种较大的转经筒,通常在围绕着寺庙的长廊上成排列放,供朝佛者边走边推动,也是转经方法的一种。转经一般是早晚两次,主要围绕寺庙、佛塔等进行,有的也在神山、圣水之间进行。
在八角街上,那些互不相识的人就像暗中被什么东西支配着一样,往往在一阵猛然的骚动之后,便开始严格地顺时针方向沿着这环行路走。无数双脚,无数双毡靴踩着路面,发出一阵阵的嚓嚓志。这涌动着的队伍带着往世世界的向往,一遍又一遍地转动着,行进着,有些神秘,有些压抑。
在转经的队伍中,有时可以看见一些衣着破旧,但神情虔诚的藏族人作一种“俯冲”式的叩拜,从他们那被磨破的衣服和膝盖上可以看出,他们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昭寺门前的。
藏族人对宗教的热诚可以在叩长头这种朝拜仪式中充分表现。进行这种“五体投地”式的朝拜要首先双手合什,高兴过头,向前踏一步,然后用双手在额、口、腹触碰一下,这表示身、语、意与佛融为一体的意思,表示全部身心的对神灵的敬畏,乞求神灵的护佑。然后双膝跪下,全身伏地,额头叩下。在指尖处作一个标记,站起跨步至标记处,再作揖下拜。
不过,大昭寺门前也并非是一个时刻让人感到压抑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其实是很放松的,即使是那些叩着长头,从很远的牧区赶来的藏族人,他们也会在闲暇的时候,坐在一旁闲聊。有时游客们将镜头对准他们,他们会很干脆地咧嘴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笑容。他们甚至还会凑上来,要求看看你的相机,和你开上几句玩笑,虽然大多数时候,和他们在语言上根本无法进行交流。
拉萨的转经道事实上有三条,一个虔诚的信徒通常会把这三条转经道都走遍。一条称为囊廓,位于大昭寺觉康佛殿外的千佛廊,是拉萨内、中、外转经道中的内圈;另一条称为八廓,围绕大昭寺的八角街,是中圈;还有一条是外圈,称为林廓,围绕药王山、布达拉宫、小昭寺及整个拉萨旧城区。
世界的中心
说到八角街就必须得提到大昭寺,它们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大昭寺修建于松赞干布时期,那是公元7世纪。据说松赞干布决定修建大昭寺以后,为了亲督统工程的进展,率领着手下的伦相大臣和王妃们先住到了涡汤湖边。为此,人们在湖的东西南北四面修建了四处房舍,给他们尊贵的国王居住,这四座宫殿就是拉萨最早的四处建筑,也就是八角街的雏形。等到大昭寺建成以后,四面八方的信徒和僧人全都赶来了。人越来越多,为了接待这些远方来客,大昭寺周围渐渐出现了十多家有旅店性质的建筑,从远方赶来朝佛和做生意的人有了落脚之地。几百年过去了,尤其是15世纪以后,大昭寺已经成了传播佛教的中心,为了满足信徒们的要求,大昭寺于是建立了僧人宿舍、宗教学校以及一些小寺庙。
大昭寺就这样催生了八角街,而八角街也就这样渐渐成为了拉萨的代名词。
这里的建筑越来越拥挤,一些虚信佛教的藏族人干脆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他们定居下来,生产劳作之余,每天能看到,亲近到自己心中的神灵,有了一种前所未有安全感。有了人,自然就有了人所需要的一切日常设施,贷摊店铺,手工作坊,政府的管理机构也逐渐完备,这里渐渐地成为了拉萨平原中心的闹市。
大昭寺最初是松赞干布为尽尊公主建筑的宫殿,在修建之初,文成公主专门运用阴阳五行说把西藏和拉萨的地形山水都测算了一遍,然后她告诉松赞干布,说西藏雪域是罗煞女魔仰卧的形状,而拉萨中心涡汤错正好是女魔的心脏,应当把寺庙建在上面,以镇邪。松赞干布欣然采纳了文成公主的建议,就把宫殿修建在了湖上。
大昭寺是西藏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并且开创了藏式平川的寺庙布局规划。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大昭寺的修缮,因此几百年过去了,大昭寺形成了召集25100多平方米的规模。
大昭寺不仅仅是一座供奉众多佛像、圣物以使信徒们膜拜的店堂,它还是佛教关于宇宙的理想模式——坛城(曼荼罗)这一密宗义理立体而真实的再见。穿过千佛廊、夜叉殿、龙王殿,数百盏酥油洒的后面便是著名的“觉康”佛殿。它是大昭寺的主体,佛堂是个封闭的院落,有四层,中央是个大经堂。藏传佛教信徒认为拉萨是世界的中心,而宇宙的中心便是觉康佛殿。大经堂正中是造型庄严的千手千眼观音,还 莲花生和强巴佛塑像。
大昭寺释迦牟尼殿廊檐下的狮子浮雕很有特色,它们的鼻子都是扁平的,有不同寻常的状貌,大家都说是因为当年松赞干布失手砍下了它们的鼻子,于是工匠们如法炮制,所以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其实,这是具有西域特色的人面狮身伏兽。
上了大昭寺的二楼,阳光照射下的大殿熠熠生辉。脚下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那是信徒们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大殿。站在顶层上,抬头仰望大殿庄严的金顶,心里有一种感动。和广场上的情景不一样,这里很安静。一群群鸽子在寺庙的殿檐下咕咕个不停,脚下囊廓内信徒来来往往,沉浸在一种迷醉的宗教氛围中。
佛供与84位驻藏大臣
围绕着八角街转经路有许多古迹。除了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和文成公主种下的唐柳,最为出名的就应该算是立在广场上的“大桅杆”和驻藏大臣衙门了。
大桅杆叫“觉牙达金”,意思是“给释迦牟尼佛的供奉”,也称“佛供”。象这样的大桅杆,八角街曾经有四个。以前,藏族姑娘只要到了十六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就会被父母带到觉牙达金大桅杆前,举行一个庆贺成年的仪式。北美洲一个叫阿帕奇的游物部落也有这样的成上仪式,用特有的方式巴刚刚成年的女子送上人生的又一个阶段。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藏族姑娘的父母往往要为她们准备好丰富的妆饰,同时要做上一项“巴珠”。“巴珠”非常漂亮,先用假头发做成三个高高的发髻。戴上头顶的时候,那三个发髻可以摆成三角形,每个发髻的顶端又系上一颗又圆又大的珠球,再用精心串好的珠链把三个发髻围好装扮起来。三个发髻靠脑后一角,还要编上一个修饰得非常漂亮整洁的小辫子。
到了举行仪式的这一天,父母一早就亲手为女儿戴好“巴珠”,然后亲手将各式各样的耳饰、项饰、手镯、指环把女儿打扮一番,让女儿第一次围上那条称为“邦典”的长围裙。最后,父母和邻居亲戚们就陪伴着女儿来到觉牙达金大桅杆前进行成年仪式。姑娘先在桅杆上系上一条哈达,再在桅杆旁边烧起香火,接着便围绕着大桅杆一圈圈地转着念经。这时,家人们便站在桅杆前向佛祖为姑娘祈祷、祝福。
这样的大桅杆现在在大昭寺门前还有,但姑娘们成年的仪式大概已经不再举行了。
供奉财神的白色香塔北面,有一栋顶部有一层红色草墙的三层楼房,这是当年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清朝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开始于清朝初年雍正年间。驻藏大臣射门驻地,曾几经变动,1751年以后,衙门便搬千到了大昭寺以北,小昭寺西南角附近。
这栋三层楼房据说很宽敞,高大坚固,容易防守。以前,这处衙门处还有园林亭台,栽有许多树木。水源是专门从外面引进衙门的。所以说即使在的当时西藏那样简陋的环境下,驻藏大臣衙门还是很有气派,而且很舒适的。在这短短的183年时间里,清朝一共向拉萨派遣了84位驻藏大臣。
我在八角街上偶然看见了这栋建筑,不过大门禁闭,门前是一些正在转经的信徒。找当地人打听,原来这处建筑一直没有对外开放。
香味街道与购物天堂
现在的八角街,成了各地游客观光和购物的集中地,就象丽江的四方街,不一样的是,这里总有种浓郁的宗教气氛。所以有时我觉得它象是一个琐碎的跳蚤市场和一个宗教圣地的混合品。
这里有琳琅满目的腰刀、头饰、手饰、嘎乌、胸牌以及有印度、尼泊尔之风佛教塑像,还充斥着各种从外地进入的其他商品。初次来到八角街上的游客,总是能闻到空气中传来的阵阵清新的植物香味,原来这香味是从八角街上那一座座白色的香塔里飘散出来的。这种香草不必加工整理,它就象是一种情感和意念的寄托物,是专门用来做佛事的。
在八角街上还有出售这种香草的藏族人,他们在白塔前面排成一行,热情地招呼你,并仔细地告诉你它的用途。这种香草长着返白色的针叶,茎杆曲曲弯弯。是在灌木丛中生长的,把那些刚刚砍摘下来的鹇草枝扔进香炉里,随着一缕浓烟,清新的香草味便立刻弥漫在空中。这种香草是藏族群众祭祀神灵、佛祖时一种很普通的香料。它一般用在外野,不用于寺庙之中。特别是在宗教节日期间,拉萨更是到处都飘扬着香草那芳香馥郁的香味。
很多游客都对这种香草很有兴趣,一个女孩子买了一大袋之后,又不厌其烦地沿着八解街走上一圈,在每一个香炉前都要撒上一把表达虔敬之意的香料。
八解街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也充满世俗生活的乐趣。在这里,一些古老的宗教习俗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相安无事的。人们按照他们习惯的生活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看见那些正和你砍价的藏族人,你会相信几十甚至几百年前,他们也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居住在八角街周围的民居里,从祖辈那里学会谋生的手艺,在自家的作坊里,制作寺庙和家庭必须的金银器、佩饰、刀具、鞍鞯、唐卡、地毯、氆氇和藏香藏纸。
西藏的唐卡很有特色,以白、黄、红、蓝、绿为主、桔红、肉色、淡胭脂、暗黑、烟色、土黄色、紫黑、翠绿和骨色为中副色,每种颜色又可分为多种分色,一般有32幅色。因此,唐卡都是色采斑斓,让人爱不释手。许多到拉萨旅行的人,最喜欢购买的就是唐卡。而出售唐卡的商店和摊贩都很多,有价格非常高昂的,也有几十块一张的。那种具有收藏价值的唐卡在一家叫“西藏唐卡艺术村”的地方有很多,老板是学美术出身的,眼光应该不错。他告诉我,说他经常开着车,到藏区牧民家里去收购,很多精品都是这样得来的。
在环行大街上转上几圈后,你不妨穿进旁边的小巷里。这些小巷中的建筑看上去似乎没有环行大道上的建筑那样豪华庄严,但却别有另外的情致。阳光从一侧的白墙上泼泻下来,骑着三轮车的居民突然从角落中转出来。他会冲着你笑,甚至会吹口哨。走进阴冷的门道,通常会有个院子,院子里总有个藏族姑娘在阳光下梳洗她们的长发。
在八角街的夜晚来临之前,我进了一家名叫“刚吉”的餐厅。它正好在大昭寺的正对面,上楼后,有个不大的平台。坐在那里要上一杯咖啡,等待着夜色渐渐笼罩在大昭寺金碧辉煌的金顶。看着逐渐黯淡的广场上涌动的人流,竟然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隐没在银光背后的手工图腾(文/小逃)
我们相信拉萨是一座真正的手工城市,到处是刀刻斧凿的痕迹。八角街所呈现的手工艺形态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延续的坚强力量,这种力量与信仰极为接近。
八角街大概是世界上色彩最丰富的街道之一,人类肉眼能够反映的色彩集中在这里展示、陈列,在恍惚的视觉陶醉中你必须有足够的理性才能将如此繁复的色彩构成区分成具体的物质形态,这些熠熠生辉的藏式手工艺品正是八角街的精髓所在。
从八角街进入拉萨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人们从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身外之物”上看见一个古老民族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执着信念,他们的佛珠、银饰,他们沾满油污的藏刀和木碗……所有初到拉萨的人都会被这些古朴绚丽的器物所迷惑,想像着这些精美物品以怎样的形态经过那些两鬓斑白的指粗大的工匠之手,还有那些历经百年的传统作坊一定就隐藏在热闹的街道之后,许多人在八角街附近不厌其烦的寻找,最后他们只找到了一些生产藏毯藏饰和各种器物的小型工厂,机器代替了手工,来自江苏、云南的小生意人成了这一行的主力。这就是八角街的另一个秘密,古老的作坊和经验丰富的工匠已在历史的演进中最终成为藏式手工艺的一部分,你无法寻到他们的踪迹,千百年来他们民幻化出的美妙身影和文化魅力已然隐没在八角街的闪闪银光之中,历久弥新。
在八角街欣赏手工艺品有两种乐趣,一种是讨价还价的乐趣,一种则是纯粹的感官乐趣,后者需要很高的鉴赏能力。比如木碗,八角街上的木碗清一色的质地光滑,色泽高贵,很像休闲屋里盛粥的时髦器物,精美成了它的首要个性。木碗在藏族中有着很高的礼遇,无论身份贵贱,怀揣木碗行走天下,吃饭喝茶都不用愁了。旧日的达官贵人中木碗既是一种装饰也是官阶大小的标志;各个寺院喇嘛们使用的木碗各不相同,所以木碗又成为识别寺院的标志。在西藏最好的木碗是“察牙”和“纳抛”,这两种木碗都是用整块树瘤车出来的,由于根瘤的木质不同,年代远近各异,花纹十分独特。据说一个上等“察牙”木碗可顶十头牦牛的价钱。
我们在八角街附近发现了几家规模较大的西藏地毯批发零售店铺,据让主介绍,如今大一点的地毯全部由工厂机织,只有少数小幅地毯是从附近农村收购的,这些纯粹的手工地毯保留了原始的民间特色,非常难得,如果买主慧眼独具,说不定能从中发现真正的极品。织有各种彩色图案的仿古地毯被称为“卡垫”,早在元初,最著名的卡垫之乡江孜就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到了清明两代,仅江孜镇就有数千人专门从事卡垫生产。这些色彩艳丽织工精细的地毯与波斯地毯、土尔其地毯并称世界“三大名毯”。
出乎我们的意料,八角街上藏刀的地们并不显眼。大概因为藏腰刀个头太大不方便携带,实用功能也日渐消退,人们主要在刀鞘的装饰性上作文章。离开草原,藏刀藏起了锋利的刀刃,成为人们欣赏把玩的普通器物。藏刀分为长刀、短刀和小刀三种,长度从1米多到10多厘米,刀把以牛角或木料制作,并缠以银丝或铜丝、铁丝,刀鞘刻有各种精美花纹,如果再镶上银饰珠宝价格就另当别论了。
西藏的传统金银手饰和五金生活用品久富盛名,现在由于商品流通渠道拓宽,这些物品在内地的很多城市都能买到,人们早已不以为奇了。到是一些造型独特的雕塑工艺品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兴趣。这些雕塑工艺品有铜铸、石雕、泥塑和木雕等,造型上既有传统的神佛人物飞禽走兽,也有极其抽象的现代艺术造型。这其中造型夸张色彩艳丽的面具最受旅游者的青睐,面具在藏语中被称为“巴”,早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就有“戴上假面具、装扮狮、虎、牛、豹等的舞蹈”,这说明“面具”已在吐蕃形成。西藏的跳神面具,戏剧面具都倾向表现和象征的艺术风格,不同地域差异明显,卫藏地区的面具较为斯文、严守法度,西藏东部康区的面具泼辣怪异、惊世骇俗。如今市面上出售的面具有很多出自真正的艺术家之手,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使面具本身呈现出一种后现代意味,令收藏者们爱不释手。在拉萨,许多流浪诗人画家把他们的工作室也称为“作坊”,用双手挣钱,用诗与画体现对西藏的理解和热爱,他们的手工劳动加入了个人尊贵的信念,所以更加人性化,这些“作坊”同样呈现出手工业最本来的面目,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真正藏式手工艺品的一部分,在拉萨的各个角落出售。
藏式手工艺品一直是八解街最丰富的构成,一种文化的延续遵循一种传统的方式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在丰富绚烂的色彩背后,藏式手工艺品正在承载这样一种使命。在拉萨不可避免地走向与现代城市共融的过程中,八解街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将两者竭然隔开了,这里所凝聚和包容的远非传统和现代两种形式,它以当街闹市的寻常姿态让每一个来访者轻意溶入其中,却在心理上永远与其保持着神与人的直线距离。碰撞,使传统愈加突现。
“藏式”自由居住(文/小逃)
藏式小旅馆是拉萨旅馆的一种独特标志,自由居住创造了旅游者之间的自在关系,拉萨兼容并蓄的气度在那里得到充分体现。
拉萨是座流动的城市,太多的外地移民和旅游者令这座古老的城市日益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开放气质,拉萨为旅游者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旅游空间,同时也被来自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文化和风俗所感染,国际化与古老的民族传统相互交融,住进拉萨独有的藏式小旅馆,这种感受就愈加强烈了。
沿拉萨最热闹的街道一路走过去,招牌并不显眼的藏式小旅馆就隐藏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店铺之中,它们都有不大的门面,中英文两种招牌和很明显的“藏式”标志。藏式小旅馆与普通旅馆的明显区别在于其馆舍建筑式样和外部装饰上是藏式的,一般是两三层的阁楼,楼梯狭长房间较小,这使得旅馆本身具有较多的公共场所,如院坝、过道及面积不算宽敞的餐厅。
拉萨有名气的藏式旅馆不下十几家,它们大多是在只有几个床位的小旅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草原牧民经营的“藏家乐”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又同时具备了欧美小旅馆的自由风范,在这里可以喝到醇正的酥油茶和地道的苏格兰咖啡,房间的布局特色是藏式的,居住方式却是欧式的,两者相得益彰的结果是使枯燥的旅途居住变成了饶有趣味的文化享受。
八廓街附近的吉日旅馆、亚旅馆、八朗学旅馆及攀多旅馆等是藏式旅馆中特色鲜明的几家,它们坐落在拉萨市的繁华地段,与附近几家三星级宾馆相比生意毫不逊色。其中攀多旅馆是一名叫攀多的藏族女子与老外合开的,这种合作本身令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中外游客都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来采访时正是旅游淡季,从苏格兰远道而来的英格兰女士已经在这家小旅馆住了近两个月,她说藏式小旅馆最初吸引她的是低廉的价位,现在她在这里找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旅途中的归属感。“在氛围独特的藏式小旅馆里文化和传统都不再是相对保守的概念,人们在狭小的空间里更容易相处,藏式居住布局让人觉得西藏不再那么遥远神秘,两种文化的碰撞变得随意和亲切,感觉很妙。有时我一连几天不出去,就在小旅馆里看书、找人聊天,能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找到旅途中的归属感实在值得庆幸”。像英格兰姆一样,许多人带着冒险的激情来到拉萨,结果却发现这座在地理和文化上同样具有非凡高度的城市首先给予他们的是一种安祥和平和,很多人从此爱上拉萨。小旅馆居住的日子英格兰姆找到了称心的旅伴,是“真正可以一起上路的人”,他们准备五月份进入后藏。
随着来拉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期间,许多地道的藏式小旅馆渐渐有了“星级”宾馆的气派,装修日益豪华,档次随之提高,小旅馆固有的特色却日渐消失了。只有一些规模较小或新开业的藏式小旅馆延续了最原始的朴素风格,深受外国游客的推崇。这些小旅馆将藏族特色与欧洲风情特意地结合在一起,每一级台阶每一处回廊看似随意又独具匠心,吧台处丰富的自助旅游信息和房间标价全部是英文,地道的藏族服务生说着流利的英语,房间价位也较低,旅游淡季在15到30元一个床位,旺季则随行就市,可能会成倍翻涨。藏式旅馆还提供周到的家庭式服务,如出租自行车、提供中西餐、提供自助旅游信息,有的还能提供导游服务。在藏式小旅馆人们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入住,成为一个松散的临时家庭,这让人们回想起美国西部的乡间酒吧和途中客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产物同样将自由风格及民族特色融入行走者的旅行生活中,使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更加随意和容易被人接受。这些藏式旅馆更多体现了旅游者之间的一种“自在关系”,使旅游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使拉萨多了些与众不同的味道。
“岗拉梅朵”的滋味(文/小宝)
拉萨的酒吧与内地相同,拥有美女、美食和美酒;还有一点不同,那里盛产“拉萨情绪”,到过“岗拉梅朵”的人深有体会。
岗拉梅朵是拉萨八角街旁边的一个酒吧。
拉萨的酒吧是会让许多人发狂的,让我给你读读她的菜单:尼泊尔小煎饼、牛肉咖喱饭、酸菜碎肉饭、藏面糌粑……,再让我给你讲讲我在酒吧里看见的美女,她们来自世界各地,她们总是拿着一瓶嘉士伯或者拉啤走到你的桌前,轻轻地坐到你的对面,看着你,让你心生绮念……哦!原来她认错了人!
虽然岗拉梅朵里的美女和其他地方的美女一样难以应付,但它确实有可爱的地方。在这个两层楼的酒吧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风格的油画作品。这些油画主要是针对老外的,老外往往进了岗拉梅朵就迷糊了,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神秘的藏族符号让他们总是忘我地掏钱,甚至激动得在刷卡这样的大事情上也会失误。当然,这也说明西方人的确更懂得对不同文化的欣赏,不象我们,老是在八角街上惦记着给小资身份的小女友买上一大堆便宜的藏族手镯或者戒指之类的玩意儿。
岗拉梅朵的老板姓孙,孙悟空的孙,他们叫他老孙。老孙长得不高,但比较帅,很有艺术家气质,就是在收钱的时候,也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这是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不仅是他,他手底下的那个“威物”单从外貌上看,也属于长得很有雕塑感的师哥:一成不变的皮甲克,修长的身材,一双致命的(对女孩而言)的冷漠的眼睛。
岗拉梅朵有了这样的老板和威特,有了满屋子的油画和上下两层楼的空间,而且还有十来扇临街的窗户,能够让你随心所欲地张望大街上往来的各族美女,这样的地方,我想凡是到了拉萨的人都会选择一个寂寞的晚上去坐坐。就算不寂寞,也会想办法让自己看上去很寂寞,因为寂寞,是一个游客感受一个城市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住在酒店离岗拉梅朵很近,5分钟的距离。所以吃过晚饭,我总是要到岗拉梅朵去坐上两个小时。在那几天里,我共计在岗拉梅朵消费了若干磅酥油茶,烤牛肉及快餐饭,其实,在这里吃饭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坐在那里能尽快地把自己融入到拉萨的空气中。想想,在一个诞生过扎西达娃、马原和韩书力的城市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文艺一把呢?
我在岗拉梅朵里坐着的时候,总是在想那个叫马原的男从当年是怎样因为寂寞而独自来到八角街上,混迹于人群中写下他那些寂寞的小说?那时,拉萨应该是没有岗拉梅朵的,所以马原只有和他的陆高朝荒原上跑。
现在还在读马原小说的人估计都是会到岗拉梅朵坐一坐的人。因为拉萨实在不象是马原在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个城市,所以难免会想象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会出现在岗拉梅朵这样的地方。那些流浪的人,那些寂寞的人,那些在八角街上流连不去的人,那些表情古怪的人和那些对空气温和的城市怀有恨意的人。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象我这样的一个日渐发胖的男人,来到拉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可以不复查布达拉宫,也可以不去罗布林卡,但如果你不让我在这里凭吊一番大师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就是剥夺了一个男人曾经拥有的梦想。
在离开拉萨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坐在岗拉梅朵里,看着光线渐渐黯淡,看着酒吧里一堆日本女孩青春的面容,想起年轻时代的马尔克斯在巴黎大道上看见晚年的海明威挽着他的妻子正在散步的情景。那时马尔克斯还嫩了点儿,居然立刻站在街道中央象个追星族一样狂呼“大师!”
说实话,我真想站在街道中央喊上一嗓子,就是不知道拉萨全市人民和岗拉梅朵里各地聚拢的小资们同不同意。
两个人的拉萨(文/张平)
在拉萨八角街的一个画廊认识了从北京辗转来到拉萨的蒋勇。他是北方人,像一只候鸟一样追寻着他的梦想。他租住在福利印刷厂招待所,那个地方长满了白杨,我们的视线越过白杨的树梢和低矮的简陋房屋,可以看见蓝天下荒芜的山峦。
去他家的时候,他的女友出门买东西去了。房间里的布置简单,墙上挂的,墙角堆的,画册中收藏的,全是他们两人这些年来的油画作品。有的是等待着送到画廊出售的,有的是纯粹为心灵而作的,是非卖品。
正聊着,蒋勇的女友张平拎着一袋东西回来了。蒋勇和张平是在北京认识的,那时张平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用张平的话来说“当时觉得不到北京,还不如死了算了”。去了北京,穷困潦倒的张平先是住在一个地下室里,每天到处奔波找工作,甚至觉得找到一个保姆的工作就满足了,那是在1997年。
就在这一年里,忙于找工作的张平被一场寒冷的阴雨逼进了北京街头的一个画廊。然后她一眼就看见了正在画廊里工作的蒋勇。再然后,他们理所当然地恋爱了。
张平笑着对我们说:“蒋勇同志是个好人,说是不能让我的才华埋没在保姆堆里,我挺感谢他的”。
但在那里呆上几年后,看的东西多了,见到的人也多子,觉得自己还算是有才华的人。北京是什么?张平说,对我们来说,北京仅仅是一个食道,或者说是一个通道。在那里没有感觉了,就想离开。
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拉萨。
离开北京后,蒋勇打前站到了拉萨。张平却先返回在湖南的老家呆了几个月,在山区里住了一段时间,每天画画,在另一种状态中放任自己的思绪。几个月后,她来拉萨和蒋勇汇合。
蒋勇和张平在拉萨一如既往地画着他们的画,大多数时候,蒋勇在画室中工作,张平就在一旁忙着家务。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药王山上,窗户外面就是布达拉宫。日子像水一样流逝,静静的,让人毫无知觉。
张平永远在她的速写本上漫无目的的勾画着一些与梦境有关的形象,旁边是她信手写下的诗句和一些飘忽的感受。蒋勇很帅,在拉萨经常有女孩子要把联系电话留给他。当然更多的时候要忙于画画,有时,也会写诗,他认为在这样的时候,自己非常真实。
在他们的隔壁,还住着好几个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室都租在二楼上。画家们都很平静,没有多少话,抽烟,喝茶,喝酒,让我们看他们最近的作品。出门时,拉萨的阳光正是一天中最强烈的时候。白杨在蓝天下没有一丝阴影,天空和大地单纯得让人感动。
这是蒋勇和张平的拉萨。两个人的拉萨,与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他们在拉萨的空间中,杜绝了对拉萨之外的世界的联想。(编者按)
我居住在布达拉宫对面的山上,看云彩和人君,这样的半年,我画画和生活。
我没有走进哪家的寺院,我只在山下的茶馆里喝酥油茶,看人群和拒绝。我看见山上有遍地的石头,石头上的经文,看不清楚的大大小小的佛像,山下的尼姑对我很客气,我盘腿坐在山上,能听见山下刻经文的匠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从不把石头从山顶抛下。
我不懂藏语,我只跟他们买大葱和土豆,只看见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环境,我很难过,不愿意猎奇,不明白。看见酥油洒的焰火,看见和生存在这里,呼吸,畏惧在这里,精通进入我的体内,是山上的短尾巴的老鼠,是看不见的猫,和生活在墙壁里的蜥蜴。我呼吸自由的一切,拒绝是我想法的归纳,亲近人,拒绝人,拒绝我,无法抛开一切的体验石头和草,却又看见他们,风大了,我不能像蜥蜴那样一动不动。看久了,眼前亮亮堂堂的一切,分不清亮部和暗部,却绝沉入沉默,我只有突然傻笑了。
蒋勇作品
终归有那么一天我只不过是一个灰尘的容器,我得离开路奔走,去找植物的尸体,希望能在它们尸体的能量上烤干湿灰,能剥下来的灰,太多的声音,我没有办法看见和听见自己。离声音远点,别的东西就会多进入一些,风吹捧着杨树叶子朝我翻过身子。果园后面的紫色山峦上一块旋涡状的云彩撕扯出一小片灰蓝的天空,突然记起回来后的第三天,晚上的一阵大风后,干净的贺兰山铁红的断层,明净的天空,一个多么好的地方,象死去的天才坟头的磷火。还有唐古拉山口的夕阳最热烈的红消失在纯净的蓝色群山里,这两个意象让人感到衰弱,这是个热闹的地方,这么多的声音让人昏迷和疲倦,又一阵风吹来,和更多的人相处,未处理的废气就在周围,这么大的原野在城市周围。我们的厄运连这身边的植物都无法拯救,是因为我们愿意昏迷,选择无可奈何的自卫,是个征兆,我可能会这样:我看见,我视而不见。我看见灰蓝的天空,但那原是透彻而又清澈的颜色。洁净,我愿意相信并奉行。心净各静。
张平作品
我心里这样想,人搬到道路两边来居住,也就开始堕落了。前年回家的时候,从镇上回家的两条路,一条新的从村子后面绕过,一条旧的从山脚下通向村子,旧路没有新路好走,很少有车子通过,回村子一路真的清静,路边的树木静的立在那,没有厚厚的灰,满眼的绿油亮亮的晃动,时不时的鸟叫声惊醒着你,提醒你这山上住着你的骨头。
人是没有主见的生物,我们的生长由我们生活的环境箍着。同样的人,我总是这样想。我心里记着很多场景,山区,农村,郊区,城市,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水和土,我一直在里面行走,象水流动和循环,像水流动,循环。看见自己的肮脏的泡沫,我只希望能蒸发上天,未知就有希望。我很担心现在的心太,不时爆发狂怒和焦躁,困兽犹斗一样厌烦。这粘乎乎,甩也甩不掉的东西。我真的希望住的离这条繁忙的公路更远点,那样我就有时间解决其他的东西,不,是避开这气势汹汹的堕落和焦躁。每一辆载重的油车,煤车,货车,每一个轮子碾出的轰鸣,每一个焦灼的人,都在合唱:无意识流动。我已经汇入这条河流,在黄昏来临时感到欢乐,最后的一顿饭吃过,睡眠就会来临,一切真实与不真实,都幻成片断交织出现,清明时,我更怀念,时间只在过去翻来翻去。
嫁到拉萨去(文/小逃)
拉萨的浪漫气质对女人始终是一种诱惑们把拉萨当作理想的极致,演绎一幕幕动人的故事。我们选择一个有点野心的女人来呈现拉萨,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与拉萨联系在一起——爱情和艺术。她的执着正是拉萨的魅力所在。
廖勤的故事在奇迹众多的拉萨也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这人性格泼辣的重庆女人在40多岁的年纪上嫁到拉萨,而且是嫁给一个小自己九岁,带着两个孩子的普通牧民后代。从纳木错湖边的婚礼开始,廖勤把自己跟 以前的生活截然分开,在拉萨,一个40多岁的女人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季吉颇纳”是廖勤开的酒吧兼画廊的名字,汉语的意思是春天使者。这个名字应该具有多重寓意,她为两个草原上长大的藏族孩子带来了春天般的母爱,为一个身心疲惫的单身男人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也为她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廖勤的名字上过许多时尚杂志,念书不多的她自学绘画和摄影,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背起行囊游历山河无数,最疯狂的举动是与四个小伙子骑摩托车经川藏公路抵拉萨,再翻越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经青藏公路到格尔木,途经11个省市到达北京再返回重庆,行程近两万公里。那一年她已经40出头了。她与西藏的比分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在廖勤谈到与藏族丈夫觉果的爱情和婚姻仍然认为那是天意。
廖勤承认自己是宗教化的女人,拉萨的神奇与她生命中许多无从解释的机缘相互契合,拉萨是她的福地。
1996年,廖勤应邀到拉萨拍一组民间艺术品照片,一天中午她与几个朋友在西藏文联的小食堂里吃饭,正午的阳光下,廖勤开玩笑说我真想留在西藏,也找个康巴汉子。谁知这句笑谈竟被朋友们当了真,他们当中有人提议给廖勤介绍一个大胡了,新华社西藏分社摄影记者觉果。一打电话,觉果碰巧去北京出差了。时间很快过去,拍摄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天晚上接近12点,廖勤鬼使神差拿起电话,她想找找那位大胡子觉果。就是那个电话改变了廖勤原来的人生轨迹,至今她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午夜12点忽然想到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她跟觉果之间从未出现过惊天动地的爱情,在一个充满奇迹的城市两颗孤寂的心很自然的接近、交融,廖勤把一切归结于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
他们相识的第二天觉果把家里的钥匙给了廖勤,自己则去了林芝。在这个单身男人脏乱不堪的家里,廖勤找了做为女人最原始的感觉,清理、打扫,手忙脚乱。临行前廖勤偷走了觉果儿子的照片,这件事同样无法解释,她不可救要地喜欢上了那个从小生长在草原,几年没洗过澡,一句汉语不会说的小格桑。后来格桑被送到成都跟她生活了一个月,廖勤说那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个月,她只做为一个母亲存在,每天她只跟小格桑在一起,他们语言不通,但他们可以用眼神用身体交流,她第一次发现生活原来真的可以这样单纯。
1997年8月廖勤和觉果在纳木错湖边举行了浪漫藏式婚礼,一个饱经风霜的汉族女人正式成为草原牧民家的儿媳妇。回到拉萨他们要面对的是具体而琐碎的现实生活,觉果生长于地道的牧民家庭,与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廖勤在生活习惯上有着天壤之别。觉果经常三四天酒醉不醒,廖勤有时一连几天找不到他,夜里三四点钟他又突然出现了,拉起正在熟睡的廖勤去转八角街;还有觉果的那些草原亲戚,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令廖勤疲惫不堪;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也让廖勤大费脑筋……婚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廖勤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沉浸在这种疲惫和琐碎里面,与觉果的婚姻让她更快更深刻地了解了藏族人和他们的生活,她矛盾过,但却没有后悔,“做贤妻良母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更何况是在另外一个民族家里”。
一个尖锐的女人更容易从平静的生活中发现自己,在与觉果琐碎疲惫的婚姻生活中廖勤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拉萨感觉”,生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一年后廖勤平静下来,她不再歇斯底里地发火,她开始像一个真正的藏族女人一样宽容地对等酒后的丈夫和毫无规律的生活。她甚至开始欣赏觉果的醉态,试着去理解一个草原男人的抑郁,有时她陪他喝酒,喝醉了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写诗,他们一起吃生羊肉,生活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乐趣。廖勤还学会了用另外一种眼光去观察觉果的那些草原亲戚,他们的面孔出现在廖勤的画里,生活与艺术融合在一起,廖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季吉颇纳就在这个时候诞生,她同时画画、做广告公司,帮别人拍片、搞摄影,更重要的是做一个藏族男的妻子和两个藏族孩子的母亲,生活为这个生机勃勃的女人呈现出特别丰富绚烂的一面。
从去年开始因为身体的原因觉果不再喝酒了,廖勤忽然觉得生活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她已经习惯了接受一个藏族男人的醉态。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廖勤习惯了每天吃糌粑,觉果则热爱上了喝咖啡,他们正打算合写一本《夫妻夜话》,向人们讲述一个汉族女人和一个藏族男人的故事。现在廖勤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季吉颇纳里,她在这里出售自己和朋友们的画,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分享自己的快乐,她想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感受到生命完美的状态。“婚姻是一种生活体验,我对拉萨和藏族人的热爱是从我的婚姻开始的,我感谢冥冥之中的这段缘分,嫁到拉萨让我对生活和艺术都有了更大的野心”。
这只是一个中年女人琐碎的婚姻生活,因为有了拉萨这样不平凡的背景,她的生活和梦想被当成了一种传奇。廖勤用自己的体验向我们证明,在正常的生活轨迹之外,理想中的浪漫果然存在。(本文转自中国西藏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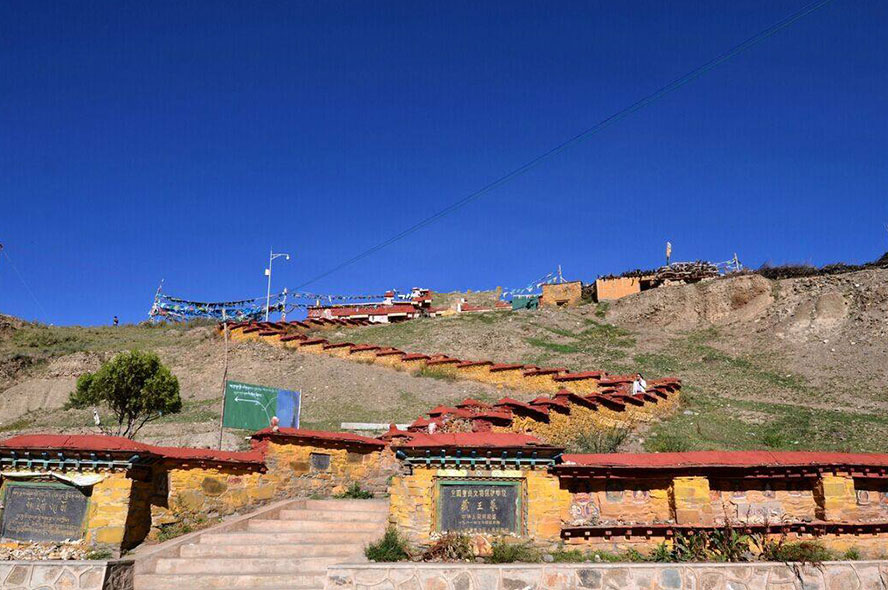






 拉萨-林芝-大峡谷-巴松措-纳木错纯玩小团6晚7日游跟团游
拉萨-林芝-大峡谷-巴松措-纳木错纯玩小团6晚7日游跟团游 拉萨-纳木错-林芝-巴松措-大峡谷-日喀则-珠峰11日游
拉萨-纳木错-林芝-巴松措-大峡谷-日喀则-珠峰11日游 2024年春节、藏历新年去西藏6晚7天旅游团
2024年春节、藏历新年去西藏6晚7天旅游团 林芝-波密-米堆-然乌-日喀则-珠峰9晚10日游
林芝-波密-米堆-然乌-日喀则-珠峰9晚10日游 西藏拉萨-林芝-新措-大峡谷-珠峰-色林措-纳木措11天跟团游
西藏拉萨-林芝-新措-大峡谷-珠峰-色林措-纳木措11天跟团游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

 info@57tibet.com
info@57tibet.com (86) 139 0891 8031 (拉萨)
(86) 139 0891 8031 (拉萨)


